咸风漫过骑楼的日子
那股腥甜,比站牌先到
走下高铁时,风里裹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——不是鱼市的浓腥,是带着甜意的咸。像刚开罐的海米在阳光下散出的气,又像晒了半天的渔网叠在臂弯里的暖。我捏了捏口罩边缘,忽然笑了,这大概就是北海给我的第一封帖,不用拆,光闻就知道是海的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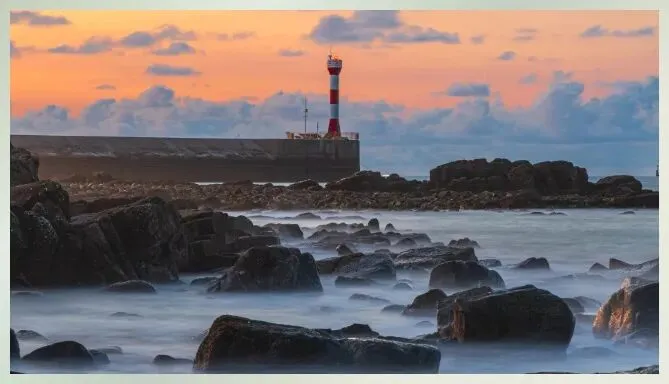
沿着站前路走,电动车的铃声在耳边擦过,像一串碎银滚过青石板。路边的阿婆坐在竹椅上择菜,竹篮里的青菜还带着露水,她抬头看我一眼,没说话,只是把竹篮往身边挪了挪,给我让出半块阴影。阳光把她的白发染成金的,风掀动她的蓝布衫角,像掀动一片小小的海。
骑楼的墙,藏着时光的屑
走进老街时,脚步不自觉慢了下来。墙皮脱落的地方,露出里面的青砖,像老人脸上的皱纹,藏着没说出口的故事。一位阿公坐在门口摇蒲扇,蒲扇上的竹纹已经磨得发亮,他眯着眼看我走过,嘴角牵起一抹淡笑,像在看一个久违的故人。

我伸手摸了摸那面墙,指尖沾了点灰,像是触到了某个年代的衣角。墙根下的青苔,在阳光里泛着绿,像时光漏下的墨。巷子里传来几声犬吠,惊飞了停在骑楼雕花窗上的麻雀,翅膀扑棱的声音,在安静的老街上格外清晰,像谁不小心碰翻了时光的沙漏。
鲜味是北海给的糖
早晨被一碗蟹仔粉的清鲜勾醒。汤是透亮的,舀一勺喝下去,舌尖先碰到的是海水的甜,然后是蟹仔爆开的细碎颗粒,像吞了一小口星星。中午在大排档点了白灼沙虫,起初看着那蜷曲的样子有点犹豫,咬下去却发现是脆的,带着淡淡的海水味,一点也不腥,像咬了一口被阳光晒暖的海风。

最难忘的是炸虾饼。面糊裹着小河虾,连壳都不用去,勺子一撇滑进油锅,滋啦一声,香气瞬间漫开。我站在摊前等,看着老板用漏勺翻着饼,金黄的颜色晃得人眼馋。咬下去的瞬间,酥脆的面皮裹着虾肉的甜,热气在嘴里打旋,烫得我直吸溜,却舍不得吐出来。旁边的阿叔看着我笑,说“姑娘,这饼要趁热才够味”,他的牙缺了一颗,说话时带着海风的粗粝。
风停在骑楼下时,我听见海
那天下午,我在老街的骑楼下找了个石凳坐下。风从巷口吹过来,带着海水的潮气,拂过我的发梢。对面的店铺里,老板在慢悠悠地擦着玻璃杯,阳光透过骑楼的雕花窗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,像一幅被打碎的旧画。

我掏出手机想拍照,却发现镜头装不下那股安静。索性把手机收起来,闭上眼睛听——远处有渔船的马达声,像谁在敲着沉闷的鼓;近处是电动车的铃铛,一串轻快的响;还有风穿过骑楼的呜咽,像奶奶在耳边讲的老故事。不知过了多久,阿婆的叫卖声从巷尾传来,“糖水哦——清补凉哦——”,我起身顺着声音走去,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很长,像一条通往海的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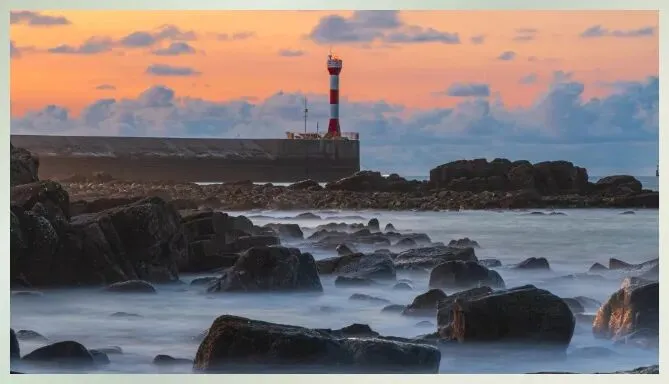
离开北海那天,我在高铁上又闻到了那股腥甜。原来有些味道,会像种子一样,落在心里。等某个有风的日子,它就会发芽,提醒你那些被海风裹住的慢时光。不必刻意记住什么,因为北海的风,早把故事吹进了你的骨头里——那是骑楼墙上的青苔,是炸虾饼的脆响,是海风吹过发梢时,你忽然停下脚步的瞬间。